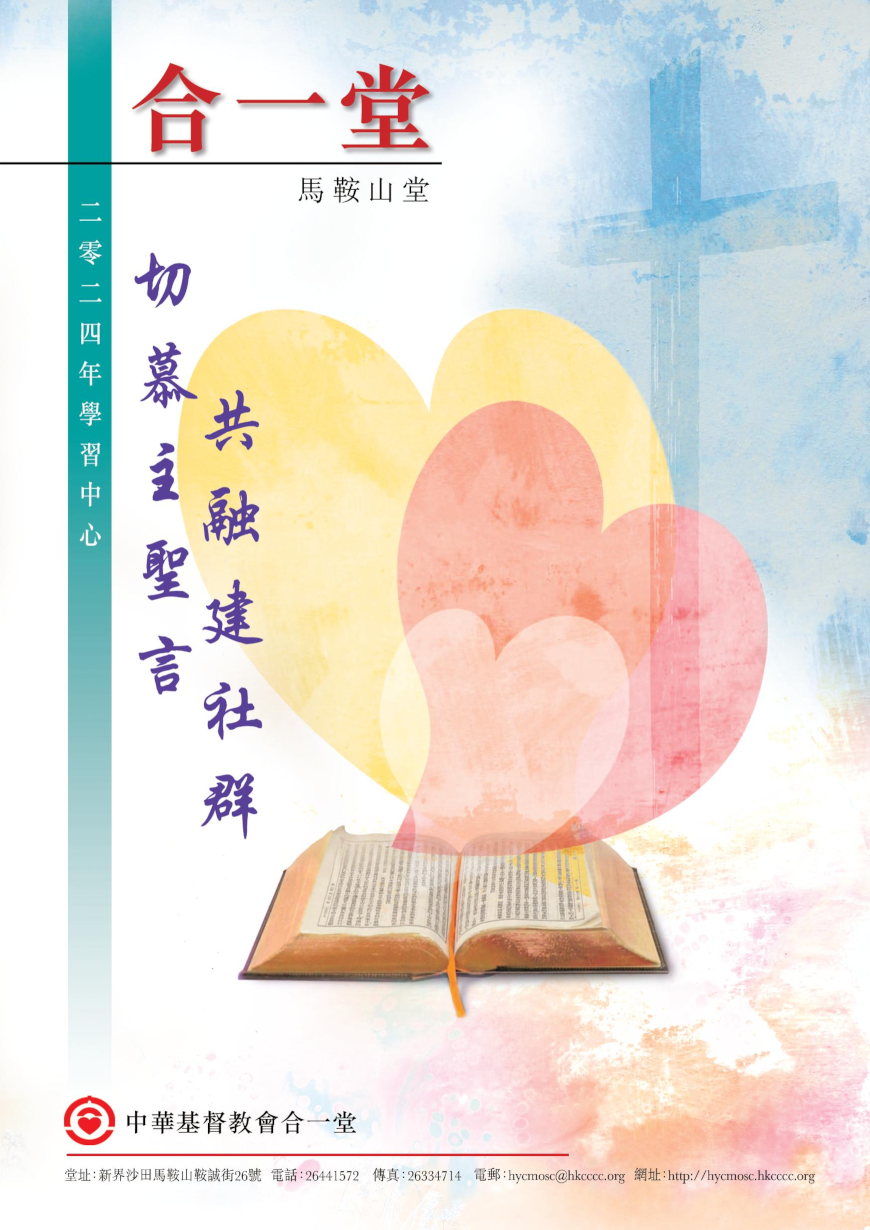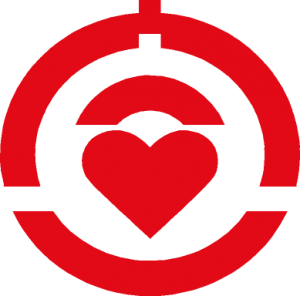【牧者分享】吳家聰牧師
馬鞍山堂2023年大齋期簡介
本年大齋期由2月22日(禮拜三,聖灰日Ash Wednesday)開始,直至4月8日結束。大齋(Lent)意思指「春天」,在春天的時候進行大齋期。整個大齋期是40天(不包括主日),因為每個主日都視作一個「小救主復活日」。復活節前的主日稱為「棕枝主日」,又是「聖週」的開始。在聖週裡的禮拜四之「基督設立聖餐日」。每年區會都進行基督設立聖餐崇拜,本年亦將於4月6日晚上7時30分舉行,將會有聖餐和彼此洗腳的安排,歡迎各位預留時間出席。
大齋期目的
大齋期的目的是透過屬靈操練,更新和強化基督徒的屬靈生命,亦是對於今天物質富裕的社會中反思其價值觀和生活態度。操練方式有不同的做法和決心,有的會以刻苦方式懺悔自己的罪惡,也反思生命以迎接基督復活;有的強調減低消費,藉以回歸簡單生活的樂趣;有的藉著捨棄一些過去喜歡做的習慣,從束縛中的「必須」獲得自由,例如減咖啡、奶茶、汽水、對身體或心靈無益處的事與物等等;亦有減少外在刺激,如打機、上網、娛樂或飲食,從而強化生命感受和覺省。大齋期不只是對個人給予屬靈生命的療癒,對其他人施予服侍來見證基督的愛,甚至教會對社區轉化來說是參與其改善與進步。
古倫神父提及:大齋期靈性操練的目標就是再度找到滋養我們的生命泉源。這個內在的泉源經常會被許多日常事務耗盡枯竭,使我們離開心靈深處愈來愈遠。sup>1 有的日程表排得滿滿,有的以飲食來填補心靈空虛,有的以外在刺激事物來使作調劑,但卻經常令泉源枯乾,中斷了與自己內心和靈魂的關係。故此,透過屬靈操練來讓我們整理一切心靈的混亂,以致泉源得滋養,得聖靈在生命引導,使生命能開花結果,春回大地。
信徒操練
教會鼓勵信徒參與崇拜及個人靈修中,信仰反省。我們由聖灰日開始派發立志咭,鼓勵信徒向主立志在本年大齋期實踐以下操練:
- 個人40天靈修:信徒從靈修中領悟聖言,靜默禱告,省察自己,並持之以恆。
- 小組分享:與所屬的團契小組或屬靈同行者定期相聚,分享靈修反思,彼此代禱。
- 實踐行動:捨己施予,實踐主愛服侍人:
- a. 關顧教會有需要的肢體,可參加教會祈禱會、探訪等工作。
- b. 參與教會對外服事的事工,信徒安排時間參與。
- c. 參與社區服事,歡迎信徒參與。
聖灰日意義
大齋期必定會有內心潔淨的時候,特別於大齋期首日安排有聖灰日崇拜(2月22日)將於晚上8時於本堂禮堂舉行。聖灰日的崇拜是標誌著我們與主一同受苦,預備心懷進入大齋期,主日崇拜是調整我們的靈性,改變屬靈生命的素質。
聖灰一方面代表懺悔,表示我們已經準備好在未來的40天,將以各種方式進行屬靈操練。懺悔意思是改善,是在這個大齋期中會比以往有改善與進步。聖灰的另一個意思是潔淨,因為以前的人會用灰燼來當清潔劑,故此聖灰象徵潔淨。在大齋期中讓我們身心得潔淨。
聖灰日崇拜注意事項
當晚會眾進入禮堂前,除了派發程序表和立志咭外,亦邀請大家在貼紙上寫上自己的名字,然後貼在胸前。本年聖灰日崇拜會有塗灰禮,塗灰儀節中在司事員指示下,當會眾逐一上前領灰時,將會獲發一張消毒濕紙巾,是用來抺自己的額頭以作消毒,預備牧者塗灰在上。如個人有帶備自己適合用的消毒方法,亦可向司事員表達。牧者會按著每一位會眾胸前貼紙上所寫的喚出名字,乃是表示上帝所看重的每一位,並會個別的向你囑咐上主的提醒。
牧者將於領受者的額頭上,用灰燼劃上十架記號,作為懺罪悔改的象徵。在牧者塗灰時,會向領受者講:「你當緊記:你本是塵土,仍歸於塵土。」提醒領受聖灰者醒覺自己從何而來,及要往何處而去,「當遠離罪惡,效忠基督。」緊記謙卑跟從主。所以,領聖灰者的信徒是以行動表示願意立志,由座位步向主的十架前領受塗灰在額上的行動,就是代表著甘心順服領受,忠心跟隨服事主。
領灰後請仍帶著額頭上的灰回家,讓家人知道你在大齋期中守節操練,讓你身邊的人作為見證與守望。
願我們透過聖灰日崇拜中的詩歌和經文默想,在主前自省和悔罪,從而在主前立志去實踐操練,並願意以行動去回應,前行領聖灰。故此,在崇拜結束時,將會收集立志咭。立志咭是分為兩部份,一部份是投放在收集箱,另一部份是自己保存,藉以提醒自己立志的項目。
約定你2月22日(禮拜三)晚上8時前到禮堂參與聖灰日崇拜:
- 領取程序表、立志咭,貼上名字在胸前;
- 塗灰前消毒額頭;
- 填上立志咭;
- 投放立志咭在收集箱中,另一部份帶回家中;
- 帶著額上的灰回家;
- 進行40日大齋期靈修與實踐操練。
本年的大齋期,但願弟兄姊妹與基督一同經歷受苦與復活,能凝聚相交,屬靈生命一同成長。在這40天的學習中,與主親近,保守善德,克己自制,服事友鄰,讓主居首位。誠心所願。
吳家聰牧師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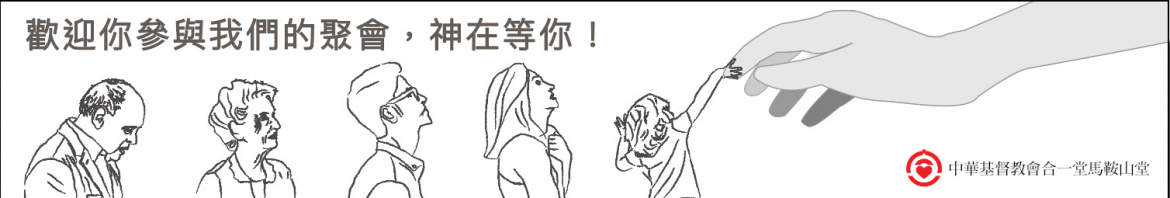





 今年年初,香港差傳事工聯會(下稱:差聯)邀請本人於「洛柔青年宣教大會:香港站」中擔任第二晚的講員。是次宣教大會的主題為「紛亂世代•賦傷前行」,而大會給予我的講題就是「賦傷前行」。相信您和我會有同樣的疑問:「賦傷前行」的「賦」字寫錯了吧,應該是「負」傷前行,不是嗎?查問之下,原來差聯刻意用「賦」的原因,乃是要突出我們所背「負」的傷痛,若果是上帝屬意賦予我們去背負的,必有其存在意義,甚至能成為我們繼續前行的動力;正如使徒保羅在哥林多後書12章所說:「我(上帝)的恩典夠你用的,因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軟弱上顯得完全。』所以,我(保羅)更喜歡誇自己的軟弱,好叫基督的能力覆庇我⋯⋯因我甚麼時候軟弱,甚麼時候就剛強了。」
今年年初,香港差傳事工聯會(下稱:差聯)邀請本人於「洛柔青年宣教大會:香港站」中擔任第二晚的講員。是次宣教大會的主題為「紛亂世代•賦傷前行」,而大會給予我的講題就是「賦傷前行」。相信您和我會有同樣的疑問:「賦傷前行」的「賦」字寫錯了吧,應該是「負」傷前行,不是嗎?查問之下,原來差聯刻意用「賦」的原因,乃是要突出我們所背「負」的傷痛,若果是上帝屬意賦予我們去背負的,必有其存在意義,甚至能成為我們繼續前行的動力;正如使徒保羅在哥林多後書12章所說:「我(上帝)的恩典夠你用的,因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軟弱上顯得完全。』所以,我(保羅)更喜歡誇自己的軟弱,好叫基督的能力覆庇我⋯⋯因我甚麼時候軟弱,甚麼時候就剛強了。」